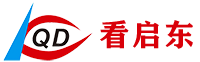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了“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美学命题,这不仅作为一种绘画策略,也体现在画论和书论之中。这种语言表达特色常常让书法学习者感到困惑。米芾曾在《海岳名言》中说道:“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逾远,无益学者。”的确如此,前贤论书,往往采用比喻、征引的方法,即用形象化的描述性语言去表达对书法的感受,而对书法的理性阐释却着墨不多。
“以形写形”的表达方式,成就了中国书论。但是也造成了中国书法笔法遗失,固守成法,宗派体系禁囿等不良现象。这在书法教育教学中尤其需要注意,如果不能批判性地吸收,可能会倾向于泥古不化,或者偏向于丑陋狂怪。因此,从表象学的视角审视,“以形写形”的表达方式能够从中把握中国书论的特点,并且采取合适的教育教学方法。
表象是客观对象不在主体面前呈现时,在观念中所保持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和客观形象在观念中复现的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表象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且对研究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例如1986 年“表象文化论”在东京大学首创。文化表象研究就是研究“表象”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实践行为中所把握的文化事象。该理论认为,无论何种人类文化,都含有各自独特的表象体系,因此,“表象”这一实践性行为无不贯穿于任何一种文化之中。
对于表象的研究定位,有些人认为它属于感觉的研究,无法达到理性的高度。其实,表象和意志是一体的,对表象的研究符合认知的规律,能够让我们透过表象,达到对表象和意志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杨九诠在《学科核心素养与高阶思维》一文中就写道,“那么‘记忆、领会、运用’三个层次,是不是低阶思维呢?就拿第一层来说,如果生成于复杂情境,‘记忆’就能成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过程中信息筛选和提取的行动策略。这样的‘记忆’,就属于高阶思维。”由此可见,在整体认知背景下的记忆是高阶思维。同理,在整体背景下的表象是一种深度的表象。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中的另一种观点“以形写神”。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因为形中寓神,神以形显,两者互为一体,不可区分,“像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所以“, 形”是一种把握“神”的途径和方式。
从总体来说,中国书论具有如下的“表象”特点,让我们在教育策略的制定方面有所启示。
中国书论采用的表述形式是“比喻”式的,而且往往一带而过,并不做具体描绘。明代书法家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写道,“拟行于云雨,譬象于龙蛇,外状其浮华,内迷其实理”,说明了这种表述的特点和流弊。例如颜真卿提出的“屋漏痕”,并未做过多的描述,后人常常不能释怀。明朝书法家李日华释曰:“屋漏雨,言相承溜下,滴滴不差移,而潴畜奔泻处有自然之变,不可预设,此在统视连行中得之。”这也是一家之言,后人常常有不同的体悟。而这种欲言又止,描写模糊,比况神奇的书写方式,成为中国书论的言语表达特征。为什么书法评论家会选择这样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是书家往往据此作为进身之阶,家传之秘,不肯轻易授人。唐朝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就写道:“设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以此描述这种状况。项穆曾写道:“独子敬天资既纵,家范有方,入门不必旁求,风气直当专尚,年几不惑,便著高声。”这也能从旁佐证。从另一方面而言,书法之形难以用语言描摹。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写道,书法“法本无体,贵乎会通”,又言“其趣之幽深,情之比兴,可以默识,不可言宣”。学书者采用的学习方法应是,“亦犹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见而以知,启其玄关,会其至理,即与大道不殊”,即摒弃感官,会之于心神,直达其书理。这样的学习方法有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取向。正是这种托物相喻、比况相类的描写手法,衬托出了书法艺术的神奇。这在一些艺术评论中也颇为常见。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保持对书法艺术的神秘感,正是书论表达的要旨。
对此的理解,即达到表象与意志的统一,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意会像,即以意义去领会表象。例如唐代陆羽《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记载:“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其中对“屋漏痕”的理解,从上下文可见,是对“痛快”和“自然”的综合表述,是对笔势的比喻,因此明代文学家、书画家李日华的理解是比较契合原意的。另一种是以像征像,通过现象的比较(可以是比喻之像和书法作品之像,喻体和喻体之像),来达到意义的领会。例如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记载:“又曰:‘力谓骨体,子知之乎?’曰:‘岂不谓趯笔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之谓乎?’”对于“趯”字的理解,多为“跳跃”“挑”。但是,我们联系上下文,这样的解释似乎并不具体和形象。颜真卿书以筋骨称之于世,趯笔不妨从其书法的典型笔画入手。如“勅”字(图1)
右边“ 力”中的竖弯钩,笔法从下按到拖行到突然提起,这样的运笔过程,显示了颜书的力量,而其中的“ 趯”笔正是这种笔锋的弹起。总而言之,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书论,才能对此有更加准确的理解。
在书法基础教育中,可以利用意象的“通感”作用,采用“打比方”的策略让学生领略其中的妙处,往往能够让学生把握住书法的主要特征以及本质规律。例如在教学行书伊始,学生往往采用楷书的笔法来书写,强调顿挫,无法体会其速度和节奏。这时,让学生比较行书的“行”和楷书的“坐”,学生就能发现行书亦侧亦正的笔画特点,以及笔画的停驻和呼应,这样的“行走特点”一经把握,学生就能“化楷为行”了。这样的方法在具体的临帖过程中,可以作为一种理解和记忆的策略。例如,篆书虽然笔法简单,但是如何让学生体会简单中的变化至关重要。因此可以让学生形成自己的“比喻体系”,归纳为“狷”“逸”“错”等不同的用笔方法,去体味不同的意趣。
纵观书论,无论是钟繇,还是王羲之,或者颜真卿,历代评论者对他们都会产生正反两种评价。例如王羲之,纵然享有“烟霏露结”“凤翥龙蟠”之誉,拥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兼之一代帝王李世民为之所作的传论,但还是会受到一些评论者的非议。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写道:“逸少至于学钟,势巧形容,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譬楚音习夏,不能无楚,过言不悒,未为笃论。”对于钟繇,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写道,“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而对于颜真卿,米芾评论为,“欧、虞、禇、颜、柳,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即使是对同一位书家,评论者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做出不同的评价。例如董其昌评价赵孟頫的书法,早年评为“赵书因熟得俗态”,晚年评为“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说明艺术作品价值的多元性,也说明了评价者的好恶影响了对书法的评价。这固然有个人的主观偏见,如米芾就对颜真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颇有非议,认为将“一字肥满一窠”是妄作。这显然是对颜真卿书论的误解。苏东坡有一语,似为解答,“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
然而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评论,也引发了学习者从“现象”本身入手,促进审美思想的自我生成。这种审美的方式是属于“现象学”领域的。徐复观曾经归纳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方法:“上面所说的‘原地能与的意识’,‘意识的固有存在’及‘意识领域’,都是超越的意识。”即能够让我们直接回到书法作品本身,将不同的论点进行“悬置”,并且通过“意识流”的共同作用,进行综合性的判断。中国书论的这种“去终极化”,以开放的面貌呈现出它的独特,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引领学习者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对象时,能回避学习对象的书法面貌,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这在教育中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不妨采取“保留”的态度去看待书法评论,一方面在临帖时选择适合自己的书体和范本,利用性格的相近性原理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临帖进行创造性的学习。纵观历代书家临《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都会带上自己的风格特点。例如朱耷临习此帖,就对笔画和结构进行了一定的夸张,形成了自己的面貌。因此,我们在注重临摹的同时,不能忘记进行自我的理解和创造,在临帖的同时,写出自己的风格。
在对待古今书法家的态度上,书法评价家往往采用“今不如古”的论点。如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写道,“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对书家、画家进行排位,便成为书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唐朝书法家孙过庭直指这种评论方式为“得其纲纪”。而后世论书,一般延循此理。有些书法家尝试对“古今”进行结合,例如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写道,“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从古法中汲取营养,也影响了清代“尊碑”的审美取向。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写道:“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他认为:“而其书碑也,必有波磔杂以隶意,古人遗法犹多存者,重隶故也。”阮元在书论中指出了“崇古”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前人书迹的失传,造成了方法的失传。那么,为什么书法这种艺术形式,如此重视“崇古”呢?为什么后人无法“超越”钟繇和王羲之呢?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书法创作历来是与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当一种书体趋于成熟,就形成了它的独特性,再加上书法精神的内隐性,难以言说,很难进行重复,因此就出现了超越难的现象。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力就熔铸成一座“丰碑”,阻挡了后人前进的步伐。
而从“古”溯流而上,再顺流而下,能够上期源头,下临无限,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面貌。这种“崇古”的方法,有其合理性。他能够形成“意识流”,达到对书法美的本质把握。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一书中写道:“这些体验通过意义关联体,通过对同一个有时这样显现,又是那样显现的,直观呈现的或在思维中被规定的对象的无所不包的统一意识,而彼此联结起来。”因此,从传统入手,向古人学习,成为一条“深得人心”的书学道路。
这对教育的启示是,可以采用临、创结合的学习方式:边临边创,或者临中有创(摩帖、临帖、背临、意临等等),达到循序渐进,古今结合的效果。一方面,我们要吸收住古代书法丰富的营养,让学生形成对“六体”的全面了解,学会容纳贯通;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吸纳其他的艺术形式,以拓展书法的学习空间。例如在书法教学中,补充徐冰的装置艺术《天书》,欣赏一些现代书法作品,或者在美术活动中融入书法主题,以拓展学生对“像”的感知空间。
对于书法拟人的发现,是书法精神的一条内在线索。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写道:“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气”“神”“势”“形”“力”等便成为判断书法作品高下的标准。徐复观曾经提出过“人伦”的观点,认为“‘韵’和骨气之‘气’一样,都是直接从人伦品鉴上转出来的观念”。这在米芾文章中也有相似的论点,他在《海岳名言》中写道,“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词”,字“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从中可见,书法精神就是人的精神。黄庭坚在《山谷论书》中更是以人喻书,“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他认为人格决定气韵,在书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又道:“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他认为用圣人之学扩充道义,以学养气节陶泳灵府,方能脱俗。“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工艺史同功矣。”他认为书法是心手相应的艺术。姜夔在《续书谱》中言道:“所贵熟习兼通,心手相应,斯为妙矣。”他认为,书学之道,就是熟练后的自如状态。中国书论中,极其强调人的因素,突出书法和其他艺术的综合性,与人的成长的同步性。
重视人的因素,在于统一表象和意志,获得两者的共同提高。叔本华曾经说过:“既是说在作为表象的世界中已为意志举起了一面反映它的镜子,意志在这面镜子中得以逾益明晰和完整的程度认识到它自己。明晰和完整程度最高的就是人……”正是这种对于人的因素的重视,使得表象和意志统一起来,使得各种审美元素综合起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确如此,一些大家虽不意于书,但由于其学养深厚,故落笔不凡,如鲁迅、傅雷皆如此。
我们的书法教育要注重广采博取、兼收并蓄。注意书法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与自身品格修养的贯通,达到“字如其人”的高度。在我们以往的书法教育中,往往仅关注于“书法”本身,而忽视了书法教育与德育、美育、智育等的关系,没有把书法与人的成长联系起来。所以,儿童有属于儿童自己的书法,不必和成人的书法完全一致。我们无需用成人的标准去评价儿童的作品,去束缚孩子的“自由”表达。他们的作品流露出来的天真烂漫、稚拙无华,也是书法“天人合一”的生动表现,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如图2)。
在书法史上,早期的书法也有这样的特点。此外,在书法教育中,不妨通过书法文化的环境布置,书法展示活动,书法家的故事演讲等相关活动,让学生在书法学习中,陶冶身心,完善神志。当然,无论是人书俱“老”,还是人书俱“幼”,都是生命在书法中的体现,都要符合人正、心正、笔正的要求。
中国书论往往是“碎片化”的,或为某一方面(例如笔法、结体等)的论述。一般的表现形式为“散论”,表达的是一家之言。采用的书写方式一般为描写和陈述,注重自己的感受,描述书体形象为主,注重方法的阐述,缺少对概念内涵的概括。由此可见,中国书论一般采用的形式是“表象性”的。当然,并不排斥在一些著作中,对于“意志”的精辟概括和独到见解。例如孙过庭在《书谱》中,谈到了“五乖五合”的样态,提出了“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黄庭坚在《山谷论书》中,提出“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清朝书法家刘熙载在《书概》一文中写道,“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等等。
中国书论对形象的重视,有其不足,也有其优点。康德曾经说过:“一个这样的事物决不能按一些自身先要从经验汲取而来的基本定律来获得;而只有我们在经验之前,不依赖于经验而知道的东西才能超出可能的经验之外。”胡塞尔也认为“直观事物本身”,才能获得对事物的重新认识。因此,中国书论中,强调了对事物表象的认识,从而达到对书法艺术更加深刻而多元的理性认识。
这对书法教育的启示是,不妨对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归纳相对完整的技法体系,从典型形象中归纳普遍规律,形成个性化的独特理解。例如,我们可以采用追本溯源的方法,归纳为古体和今体类;也可以以用笔的方法归纳为方笔、圆笔类;或者以风格特点归纳为秀逸和雄壮类……在归纳的基础上,加深对书法的概念认知。我们也可以采用理性的分析,运用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升对书法形象的认识。当代书法家采用了笔迹学、结构学、哲学等方法对书法进行研究,能够提升我们对书法的理性认识。
当然,中国书论的表象还有许多方面。我们采用表象学的视角,能够看到更多特点,也能帮助我们的书法教育获得良多启迪。